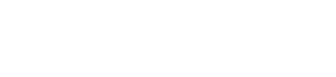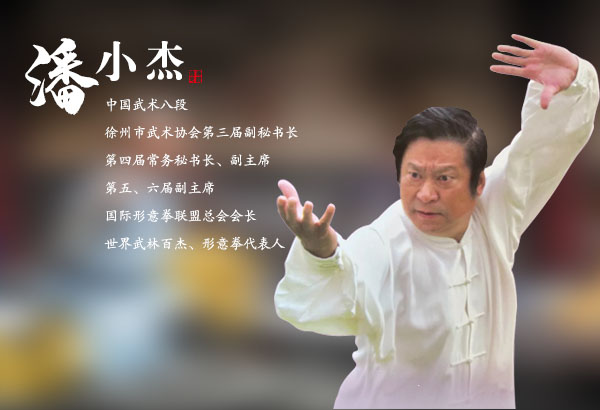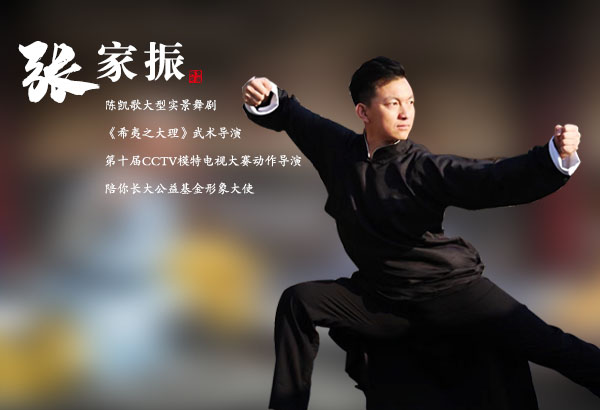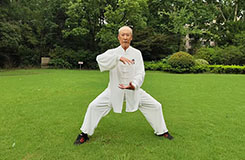武术技击:从三界理论看其精神本质
发布时间:2025-07-08
来源:平和言语 浏览次数:1095
武术:没有正解
武术本质属性是技击,有关技击研究也相对深入,但在武术技击真与假的论辩中仍留有存疑。为解析武术技击的想象性生产,探究精神分析视域下武术在三界的实存与关系,本文围绕拉康/齐泽克的三界理论即实在界、想象界与符号界与三客体a、S、Ф(Phi),结合三界理论、小客体、意识形态、驱力、欲望等对武术技击的主客体展开精神层面深刻剖析。结论:坚守内外合一的精神世界是武术技击健康发展的终极目标与路径。
关键词:武术技击 精神分析 三界 客体 意识形态
武之本乃技击,然技击善打,讲攻守,蕴术道,含韬略,其义颇深。观武术学界对武术技击的研究,多围绕武术实存表象,或致胜或舞美。学者在《中国武术文化生产中》提出了格杀之剑到文化之剑的演变以及武术文化生产的空间,基于此,本文在文化生产的基础上,对武术技击的想象性生产的精神世界新空间进行进一步探索。本文立足武术技击,以精神分析为切入点,围绕拉康/齐泽克的三界理论即实在界、想象界与符号界与三客体a、S、Ф(Phi),结合实在界原质、独一无二的小客体、意识形态、无意识、驱力、欲望等对主客体展开精神剖析,旨在逐步通过精神分析机制揭开武术技击在精神世界实存的真面目。同时,精神分析的新视角将把武术技击以全新的图景镂刻至武术文化研究的新雕版。
1.武术技击的主体研究
1.1“武术之打”困惑的解
技击是武术独立于其他运动而存在的本质属性,然而关于武术是否能打,却广遭质疑且愈演愈烈。鉴于此,有学者用辩证的观点来解释武术技击弱化、武术由拳向操化以及“武术之打”的真实与困惑。面对质疑,武术技击被悬置,不但被悬置于套路比赛的技击之“舞”,而且被悬置于高手在民间的技击之“囧”,以至于民间传统武术面对现代格斗所表现出来的窘境以及竞技武术运动依靠动作标准评判高低。在技击的场域里,武术尴尬立身,何为其解?那究竟武林确实已经逝去,还是辟谷山涧而独善其身,其“见血封喉”的绝技到底以何面目存在,又将如何示人?
论及武术技击将如何示人,则必将在精神分析的世界里寻求武术技击的多面形态,我们所能视听感知并身体力行的实在界,未能感知却萦绕存在的想象界,以及其纷繁复杂秩序的符号界。三种面目互通有无,任其形态千变万化,却始终无法逃逸无限广阔浩渺的想象空间。
在武术形态中,武术经典传说恰恰构成了武术人对武术神话的欲望,它构成了想象界武术技击的最初形态。回看武术技击实在界荒芜的以及武术以技击在符号界秩序的标榜,武术技击在想象界与实在界发生了颠覆性错位,这种错位的直接后果就是武术技击在符号界彻底的颠覆,这种秩序的颠覆就是我们最初对“武术之打”真实的质疑与疑惑的原因,秩序颠覆回答了武术尴尬立身的原因,重要的是秩序颠覆为“武术将以何面目示人”提供了解。
秩序的错位与符号的颠覆是武术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技击生产的副产品,针对武术打的困惑,古今有之,从未断绝。这种喋喋不休的争论来源于武术技击在符号界“秩序错位”的困惑,来源于武术想象界技击理想的乌托邦与实在界“沙漠”。那么,困惑的无形推手,想象界的技击神话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产生机制是什么?
在通讯信息远不及当下的封建社会,言传身授几乎是武术传承的唯一途径。口耳相传的传说类似于今天武术研究的口述史,它在当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充当了在古代武术技击的乌托邦理想下主体欲望的客体。相比于古代对欲望的填补通过传说,现代欲望的客体则极为丰富,包括现代视听传媒等现代媒介。传说与现代媒介恰恰填补了欲望的空缺,编制了想象界武术。岳飞与心意拳的渊源是拳与英雄的结合,金庸小说武侠剧中的武侠与神功是拳与侠的结合。英雄和武侠就构成了传说的主要内容,同时构成了欲望的客体,成就了想象界的武术技击。李小龙、成龙、李连杰分别被视为塑造了“功夫武侠、平民武侠与文化武侠”,三位功夫明星充当了主体欲望的外在客体。其中,欲望与幻想的缺位作为内在匮乏,传说与媒介作为外在客体,内外的互补性表现为主体匮乏需要客体满足。客体因主体而产生并具有幻象意义,同时填补了主体自身的缺失。欲望客体是永生的,在当下的今天它是媒介,在遥远匮乏的时期它是传说。
综上,关于武术之打的困惑,直接产生机制是想象界与实在界的错位进而导致符号界秩序的颠覆。其根源是武术技击主体的内在匮乏与外在的欲望的客体对主体的补充。现代学者对武术打的困惑产生共鸣是武术技击在秩序颠覆后的直接后果,困惑的疏解路径在于武术技击在实在界与想象界的平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太极阴阳学说已经高度概括了实在界之实与想象界之虚以及其中辩证统一的哲学关系,其中太极图最为形象且是为“武术之打”困惑之解。
1.2武术技击的三界
三界是精神分析中的实在界、想象界与符号界。基于拉康对三界的解释,齐泽克对三界理论进行了更加多维的解释。人类文化实践产生的武术技击同样拘泥于三界,且分别示人异面。实在界素面示人,以创伤性为特点,将物质的纯粹、丑陋与恐怖毫不遮掩地公之于众。想象界在一定程度上将个体的社会现实立体呈现。符号界则犹如悬在实在界上面的一张蛛网,符号秩序在“调停”和组织人类实践。
实在界的技击在剥离文化价值与竞赛游戏的外衣,其真实的意图则会彰显其最为恐怖的面目——胜败与存亡,绝不是重在参与、友谊第一,这也是武术不同于其他现代体育竞赛项目的精神内核。追溯到武术发展的起源之一田猎,即可看到其发生发展的原始驱动力,战胜猛禽野兽才能获得食物,才能维系族群的繁衍生息,此时技击决定生死。奴隶社会通过总结经验,技击格斗仍在部族战斗过程中渐渐成熟,为了战胜其他部族,保全自己部族,此时技击关乎存亡。封建社会中局部的斗争逐渐发展为军事阵战与个人武艺,成规模成体系的技击应运而生,从而满足军事战争与早期的教育,军事战争中的生死胜败更是直接决定帝王权利,动辄百万军士丧命于帝王的权利争斗,技击的实在界创伤贯穿始终,生死存亡,不绝于史。
想象界的技击,可以理解为广泛存在社会现实中的技击攻防,尤其发展于个人武艺的蓬勃发展,技击的社会现实是被无限放大,甚至被搬上了神台,博大精深使中国武术享有无上荣光。然而,在实在界的基础上,想象界的技击到底走到了多远,以至于现实好像遮盖了真实。实际上,现实也未必真实,想象界的武术技击已经被主体与客体在交互作用中走向信用的终点。随着社会的发展,真实对抗的逐渐消逝,想象的对手应运而生。对武术主体来讲,无论是精英阶层悬浮的学术操练还是民间民众思想对武术技击的体验,无论操练与体验是传统武术还是竞技武术,无论是在想象界还是实在界,它都应该还原技击实践。
技击是武术在符号界秩序的体现。技击产生于主体与对手之间,是二者之间出现麦格芬式对抗的流转,与运动竞赛不同,在社会秩序中竞赛在胜负过程中,主体与对手之间不产生关乎存亡的生死对抗。然而,武术技击的雏形不同,它的秩序在成败中关乎生死。武术技击与体育运动在社会秩序的大网中各自占据独特的位置,各自发挥自己特殊的作用,前者攻防格斗,后者竞技娱乐,虽然当下武术被归为体育范畴,但武术与体育仍在符号界中存在质性差别。在体育符号的秩序下,武术技击正在失去自身的意义,其原本真实的技击符号正在或已经被新的仿真的技击符号所代替。这个仿真的替身就是在普遍意义上失去了武术之打的武术套路。这种秩序的颠覆与仿真的替代导致了武术与武术文化甚至武术套路概念的混用。由此,对武术相关概念的定义与使用,需在符号的网络中精准入位。武术技击符指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面对极速崛起的现代化媒介,超越了传统文字、图像,VR所建立的虚拟仿真世界,武术技击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潜藏了巨大的机会,利空的同时是颠覆性的逆袭。未来,我们应当全面客观评定武术技击的符号所指。
总之,武术技击在三界的存在形态并非完全独立,存在共通关系,其中每一个都蕴含其他二者因素。实在界的完全遭遇都是创伤性的,想象界武术技击主要体现其无意识特性,符号界武术技击是符号秩序的集中体现。
1.3武术技击的三界屏障
在思想上对武术技击的认知,无论是绝对孤独还是相对疯癫,都或多或少涉及实在界与想象界屏障。实在界原质对想像界现实的占据发生精神孤独,“疯癫”则源于想像界现实对实在界原质的占据,屏障对现实的存在起到了重要作用。齐泽克将“车窗缝隙”这个屏障解释为保持最低限度的“常态”的前提条件。通俗一点,可称为是“度”或“阈值”,需把握好实在界的与想像界相互占据的“最低限度”,否则会出现“屏障”的土崩瓦解,现实将因遭遇实在而丧失。在三界及其矢量循环(实在界→想像界→符号界→实在界…)中,武术技击的进一步演化也将由实在界、想像界与符号界及其矢量结构来完成。
实在界与想象界之间因屏障存在而相互隔离,保持相对独立,屏障是实在界与想象界相对恒定的保障,防止二者过度渗透。武术技击的实在界与想象界同样存在这样一道屏障,从而防止二者相互渗透。看似与对武术技击的认知毫无瓜葛,但恰恰能够在精神的世界里精准剖析“打”的困惑与矛盾的来源,挖出始作俑者。想象界武术技击如果透过屏障发生对实在界武术技击的占据,则会出现对武术技击“类似疯癫”的过度神话。鉴于此,“武术之打”与“武术异化”的困惑是否发生了屏障破裂的相互渗透?借助现代技术,金庸武侠小说不但以文字影响思想,更能通过视觉影视等直入现实。将想象界的武侠功夫神话直接搬入社会现实,使之成为了荧幕上的真实,它巧妙地避开屏障,比任何时期的功夫传说都更具穿透力。面对想象界的渗透压,实在界的武术技击在重压之下被穿透,想象溢入实在。
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伴随着社会的空前发展,主体更加频繁与深刻的受到客体的影响,会偶现对现象判断的失真。因此,要时刻清醒,辩证统一,不在想象中迷失,不被现象所左右,把握真实与想象的度与界限,客观认识与评价武术技击,从而不致于“疯癫”。关于高手是否在民间尚未可知,但神话一样的迷与传说的确是想象空间的产物。面对武术技击的困惑与武术技击在三界屏障中的“度”的失衡,屏障在此显得更加重要。想象界技击的高手永远领导着实在界技击的激情,同时又得到实在界技击坚实的支撑,武术的想象界技击与实在界技击要隔开在屏障两侧,分立于两界。
三界的屏障将三界以断裂的形式隔开,并展现为实在界的武术技击、想象界的武术技击与符号界的武术技击。武术技击实存于实在界技击(Real),其“困惑”源于想像界技击(Imaginnary),其言说再现于符号界技击(Symbolic)。屏障是一种“度”,是两界互存状态下最低限度的平衡,即现实中包含一定的实在,能够反映一定程度的实在界武术技击。最低限度的设定是要技击在实在界和想象界保持良好界限,从而剥离溢出到实在界的想象界产物,促进武术技击实在回归。
1.4武术技击中独一无二的小客体
符号界的武术技击同样以某种方式陷入了符号网络之中,武术技击被视为“打”。符号界对武术技击的标记,永远不能完全对实在界的武术技击进行完全的表述,总与技击原质存在一点区别,这个剩余就是小客体。在武术与其他身体运动项目之间比较,之所以争论不休,是深埋在主体内部独一无二的技击小客体。齐泽克认为欲望的客体无法直视,小客体是欲望扭曲的凝视,是空无的、剩余的。莎士比亚借助绘画的隐喻:“正眼望去,一片模糊。斜目而视,却可以看到形体。”从一个角度观看,看到了事物的清晰而具体的形态,直接看去,看到的只能是模糊不清的一片。只有从“某个角度”观看,即进行有“利害关系”的观看,进行被欲望支撑、渗透和“扭曲”的观看,事物才会呈现清晰可变的形态。这是对小客体(即欲望的客体-成因)的完美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客体即欲望设置出来的客体。只有借助被欲望“扭曲”的凝视,才能察觉其存在。然而,我们立足三界,窥视独一无二的武术技击小客体,它究竟是何种形态?它是一切有关技击正面描述的溢美之词,它是武术人心境中对于技击的执着与无与伦比的期望。
2武术技击的客体研究
如何理解三界的关系?齐泽克借三个客体作解。符号a、S、Ф(Phi)分别代表麦格芬、流转的交换客体、不可能快感的沉默化身。在解释三个客体之间的逻辑关系时,拉康做了详细分析,符号界→a→实在界→Ф→想象界→S→符号界…。在三界的逻辑关系上,齐泽克提示,在例如“想象界的象征化”加以理解。麦格芬(object petit a),是象征秩序中心处裂缝——是匮乏,是发动了阐释的象征性运动的实在界空洞,是需要被解释、被破译的秘密的纯粹表面,它无关紧要,仅发动故事;流转的交换客体是S,是不能被缩减为想象镜像游戏的象征客体,从而它划定了象征秩序饶之得以构建的不可能性之处——它是启动象征结构的结晶过程的微小因素,是一种实在界的剩余;Ф(Phi),是实在界在冷漠麻木的想象性客体化,它为不可能的快感赋予了躯体,巨大的、压迫性的物质,仅仅是一种不可能的快感。在武术技击中,客体Ф、S、麦格芬又分别赋予了其新的想象空间的意义:技击的无极、动作的流转与虚空的对手。
2.1武术技击三客体:Ф、S、麦格芬
客体Ф这一不可能的快感,介于实在界与想象界之间。不可能的快感与“死亡驱力之娱乐至死”相对应,强大、压制而并非虚无。其中“不可能”是描述体量无穷大,主体欲望永远处在膨胀与极限边缘,永远没有极限,可称为“无极”。始于“无极”的欲望,武术作为“事件”的产生,在实在界与想象界的关系中存在着“文化欲望的客体”,并可通过客体检视主体。武术的技击性传之神乎其神,欲清楚武术的终极形态,可将“武术”作为“人文化成”之客体,其“技击欲望”则具备“无极”的特征,展示主体对技击的无限想象的欲望。在武术技击想象生产的过程中,客体Ф这一不可能的快感就是技击的无极。
流转的交换客体S介于想象界与符号界之间,是实在界的剩余,想象界的技击无极在符号化进程中产生符号意义,占据位置,获得秩序。在武术技击的实践中,身体技击动作与套路流转于主体之间,产生攻防意义,称为事件并获得秩序。想象的终极技击欲望获得了“攻守”秩序,并形成丰富的拳术拳理,犹如符号蜘网高悬与实在界主体之上。在武术技击的想象性结构中,客体流转的动作支撑了武术技击在想象界的存在,流转的交换客体S作为动作塑造了攻守双方的技击形式。
麦格芬客体介于符号界与实在界之间,具有很重要,但什么也不是的特性。“无极”的技击欲望,要实现攻防流转,总要一个“虚空”存在的对手,这个并不存在的对手很重要,“虚空”占据了实在的符号界秩序。对手是无极技击与攻守动作的载体,没有对手就没有无限技击的想象性生产,更没有真正行动意义的攻守流转动作。因此,在想象性武术技击生产的过程中,虚空对手这一客体先于攻守动作与无极技击的存在。在武术的想象性生产里面,客体麦格芬就是这个发动攻防与技击的虚空的对手,它虽然无形,但至关重要。
2.2武术技击的象征回路:技击链与高手
高手在民间还是高手在想象的空间里?事实上,高手已经先一步在想象的空间里铸成。在主体的想象性空间里,三客体已经完成了炼成高手的技击链。高手在与对手的不断攻防流转中渐入无极。
主体与客体,其中包括了技击双方与攻防流转,二者在流转交手的实在界经验上产生了想象界与符号界。想象界“虚无”的对手是主体技击的客体。经想象技击的对抗性客体流转(这里的客体是对抗性反应客体)而落座于符号界,并形成武术技击的符号界秩序。如象征层面的阐述“一封信总抵达其目的地,主体在“虚无”的对手那里会收到了自己的信息”,发现了自我,并通过修炼,完善自我。符号界的技击秩序成为连续攻防动作生成的重要条件。然而,实在界对抗性应答都具有延迟性,想象性技击则可以通过回路巧妙的解决这一问题,于是,技击链中的无限制交手渐入“无极”,在客体的作用下,武术生产了技击“高手”,“高手”的生产也契合了武术修身之“道”。
2.3武术技击的终极变体:脱“打”为“演”
武术本为实在界的基础上所做的技击的想象性生产,其历史的形成发展与武术技击主体精神、意识形态的自在自为密切相关。简而言之,武术的发生发展取决于人,属于技击类文化的产品,因其所处环境因素而融入了民族特色的符号界秩序,继承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丰富拓展了本体的同时烙下了深刻的民族符号。
传统武术技击“打”的衰微与竞技武术“演”的迷惘,从另一个角度阐释:竞技武术是武术技击的经验流转于想象界与符号界,再次生产的实在界变体。然而,在“道”的生产过程中,如明戚继光对“花架子”与“满片花草”的批判,恰恰契合了精神分析“弃绝享乐不可避免的产生一种剩余享乐,拉康称之为小客体a”,主体竭尽全力地弃绝“演”,却恰恰生产了“演”。最终,竞技武术始于主体与想象对手之间展开的技击,经对抗性客体的流转,占据符号界位置秩序,在实在界形成“技击想象”的终极变体,在淡化对抗的时代,与“脱抢为拳”的方法变化不同,武术技击性攻防“脱打为演”是质的弱化,它陷入了想象性技击生产的深渊。最终,想象性技击的操演在实在界中得以实现,并以打的技击变体的形式入位符号界。
三客体是主体异化为终极变体的必备三要素,即“无极”的技击、“流转”的攻防与“虚空”的对手。在主体与“虚空”的对手的较量中,技击链与回路不断通过流转动作升级武术攻防秩序,达到技击无极是武术想象性生产的必然结果。这个路径必然导致终极变体——竞技武术的产生,最终武术技击脱“打”为“演”。
3.结语
花盆不生猛松,鸟笼不养雄鹰,主体想象的精神世界是武术技击生产的广阔空间。短兵相接的刺杀瞬间,技击从想象界直抵实在界,红缨滴血的赤红则标定了符号界刺杀。技击的原质是格杀,格杀取自原乐,原乐直指技击格杀与娱乐至死。武术原始的技击或是走在追求原乐的路上,而这种原乐的替代品就是王权、欲望与匮乏,最终完成对物的占有。相比之下,技击的实在界指向是格杀,武美的实在界指向娱乐。无论是格杀还是武美,都在指向武术是主体内在匮乏的外源性替代物,内在的缺乏囊括人的欲望,驱力与力比多,需要外源补充。从这一角度理解,想象界的缺失,最终造成了实在界格杀。综上,精神分析视角下,武术技击也许是内在的原乐驱力与欲望匮乏下,产生于实在界的格杀、武美等物化产品。
跨文化的普遍性观念诠释了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中意味着不同的事物。然而,普遍性与例外同时存在,例外是结构性的必须。则意味着,同一符号在不同群体中的所指不同。石之美者谓之玉,在武术属性的诸多所指中,技击性是与其他文化区别的标志。技击也应当始终是中国武术众多文化符号标定下的特有标志。技击作为中国武术的最显著特点,其发展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武术实存的凋零,正如《逝去的武林》,渐成既往,雪藏于无限的想象界与符号界的文字言说之中。
参考文献:略
声明:本网站发布的内容(图片、视频和文字)以原创、转载和分享网络内容为主,如果涉及侵权请尽快告知,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删除。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如需处理请联系客服。电话:19955260606 13965271177。
本站全力支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实施的“极限化违禁词”的相关规定,且已竭力规避使用“违禁词”。故即日起凡本网站任意页面含有极限化“违禁词”介绍的文字或图片,一律非本网站主观意愿并即刻失效,不可用于客户任何行为的参考依据。凡访客访问本网站,均表示认同此条款!反馈邮箱:603516977@qq.com。